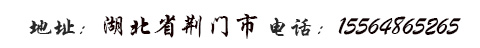2017年第2期求索特稿李永东鲁
|
原载《求索》年第2期 李永东,年生。文学博士。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等4部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发表论文约篇,20余篇被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等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等课题。入选“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重庆市高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等。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摘要“西崽”是中西文化并置、混杂的结果,是半殖民中国主奴社会结构孕育出的一类人物形象,具有二重人格,既自大又自卑,既媚外又惧外,既洋派又守旧。鲁迅信奉中西文化的优劣差序,厌恶“染缸式”的混合,故对社会身份、文化心态处于华洋、主奴之间的“西崽”极为不满。鲁迅对中外冲突的解读,把殖民暴力事件转化为“文明”问题,而在与林语堂的论争中却把民族主义作为武器加以运用,借用超强的民族政治话语构设出林语堂“为王前驱”的“西崽相”。对“西崽”的批判,释放的是知识分子的殖民性焦虑。讨论“西崽”问题时,尤其涉及到民族主义超强话语的使用时,只有回到现代中国的半殖民文化语境,才能做出理性的解读。 关键词西崽;鲁迅;半殖民;民族主义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半殖民语境下的民国文学研究”(SWU);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城市的文学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14BZW) 引论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是中西、古今文明并存的社会。“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中西文化矛盾并存,“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许多事物挤在一处”,“只能煮个半熟”。这种半殖民半封建文化语境孕育了有着“二重思想”和“二重人格”的人物类型。这类人物“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见了洋大人,他的中国人那一套出笼;见了中国人,他的洋大人那一套出笼”。这类人物被世人称为“西崽”,他们属于中西、新旧文化一锅炖且只“煮个半熟”的人物。 何谓“西崽”?“西崽”一词是由英文“boy”、音译“仆欧”和汉语“侍者”音义结合而产生的(粤语“侍者”读音与“西崽”同),一般是指洋行和西式餐馆、旅店中服杂役的中国人。因杂役身份低下,再加上在洋人手下做事,故“西崽”一词往往带有贬义,并衍生出“洋奴”的含义,其对象范围也因此进一步扩大,包括了西崽、巡捕、学贯中西的“高等华人”以及媚外惧外的政客等人物。“西崽”是中西文化并置、混杂的结果,是半殖民中国文化人格的一种人物类型。 文学中的“西崽”最初是指一类职业,20世纪后才成为具有特殊文化人格的一类形象。鲁迅、林语堂、胡风、柯灵等作家都对“西崽”进行过构形。鲁迅与林语堂还在“西崽”问题上有过一次激烈的交锋,互相指责对方为“西崽”。由于作为文化人格的“西崽”是半殖民中国的投影,“近洋”“崇西”的知识分子、买办通事、军阀政客同样难以与之撇清干系,因此,关于“西崽”的论说便进入了半殖民与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的话语系统。 文学中的“西崽”形象 提到文学中的“西崽”形象,许多人会想当然地把它归于鲁迅的首创。实际上,作为一种文化人格的“西崽”形象,在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中已出现,小说中的劳航芥兼有“假洋鬼子”和“西崽”的文化人格。劳航芥进过洋学堂,到日本、美国留过学,回国后在香港做律师,后因朋友介绍,到安徽给黄巡抚做顾问官。劳航芥熟悉洋务,以洋派头为傲,讨厌华装。但是,劳航芥在上海遇到妓女张媛媛后,为了投其所好,换上了他所讨厌的华装,并装了一条假辫子,以“中国人”的面目出现。到了安庆,又恢复了“外国人”的装扮,引得安庆街上的民众议论纷纷。这是劳航芥属于“假洋鬼子”的一面。同时,劳航芥也有着“西崽”的文化人格。他因在香港时与上等外国人有些往来,故“自己也不得不高抬身价”,并想:自己是“在香港住久的人了,香港乃是英国属地,诸事文明,断非中国腐败可比,因此又不得不自己看高自己,把中国那些旧同胞竟当做土芥一般。每逢见了人,倘是白种,你看他那副胁肩谄笑的样子,真是描也描他不出,倘是黄种,除日本人同欧洲人一样接待外,如是中国人,无论你是谁,只要是拖辫子的,你瞧他那副倨傲样子,比谁还大”。中国各地,他认为“只有上海,经过外国人一番陶育,还有点文明气象,过此以往,一入内地,便是野蛮所居”。劳航芥瞧不起中国人,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到过外洋”的有钱有权有势的中国朋友,方能成为他“心上崇拜的人”。劳航芥这种崇洋媚外、耻为华人、“事大”“事强”的奴才心态,与鲁迅、林语堂后来所批判的“西崽”非常近似。 “西崽”的构形不是始自鲁迅,也不是终于鲁迅。胡风、林语堂、柯灵、钟子芒,以及日本作家池田幸子都曾为“西崽”造影。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中,西崽主要不是作为一种职业形象来塑造,而是作为一种文化人格和心态来呈现,并且被纳入中日战争、殖民文化与民族主义的表述框架中。胡风的《“西崽哲学”》()和池田幸子的《西崽的故事》中的“西崽”在文化心态上较为接近,有着半殖民中国的“二重思想”。《“西崽哲学”》中的西崽会说英文,畏惧洋人,同时讲究乡间的“老规矩”,是位“国粹主义者”。《西崽的故事》中的张忠明有着“西崽”的种族意识和文化观念。他染上了洋人的一些习性,经济拮据却自己掏钱买鱼喂洋主人的猫;他同情谎称南洋华侨的日本人鹿他,因为他误认为鹿他是西洋人和华人所生的“杂种”;他瞧不起白俄,鄙视白俄太太没见识,把普通中国瓷器当宝贝,但受了白俄太太的无理欺压却不敢去争辩。 《“西崽哲学”》和《西崽的故事》对“西崽”的身份定位虽然近似,叙事的态度和通达的主题却大异其趣。日本反战作家池田幸子的短篇小说《西崽的故事》以年日军进攻上海为背景,对西崽张忠明的画像,交织着仇恨侵略与同情难民、民族自卑与自强的复杂情感。张忠明痛恨“东洋人”,因为东洋人侵略中国;他对战乱中的难民抱有同情心,把自己的裤子送给逃难的穷人;他关心抗日前线的战况,听说打下了几架日本飞机,便欣喜若狂;但听说上海南市被日军占领,大批难民深受战火之苦,他又为此痛哭流涕;他乐意为抗战尽一份力,买救国公债。但他缺乏民族自信心,受到洋人欺负时,只能一味忍声吞气,并痛苦地承认“没有法子,中国人是不行的”,“中国人太弱了,太老实……中国人无论什么时候都敌不过人家的”。胡风的《“西崽哲学”》的主要内容为西崽如何处理自家小孩与“绿眼睛黄头发”的“上等种”和“上等人”的孩子的冲突问题,由此引申出中国人的“不抵抗主义”人生哲学,暗讽“一·二八”之后国民党政府对抗日言论的禁锢。胡风在作品中把西崽和当局都看作崇尚“国粹”、畏惧洋人的“西崽”。 柯灵的《西崽世界》()同样由职业的西崽谈起,描画出西崽的文化人格,进而把孤岛上海的大小政客纳入“西崽”的范围,批判了“西崽”的奴才心态,呼唤中国人“挺起脊梁”。西崽自己的“阶级成分大约属于无产阶级”,但极为势利,对人“有时出奇地谦卑,有时又出奇地骄傲”——在洋人面前谦卑,在穷人和乡愿面前骄傲。除了洋主子,西崽“自信是天地间最完美的人”,他们的“不调和的恭顺和傲慢,揉合起来,正是一颗紫色的奴才的心”。上海孤岛的大小政客亦是“西崽”,他们自我膨胀,“忘记国籍,拜敌人为干爷,自己是中国人,却说得中国毫无希望,变成阿Q嘴里的‘里通外国的人’了”。 综合几位作家对“西崽”的塑形,可以把“西崽”的文化人格概括为:崇洋媚外,又因近“洋”而在华人面前显露出个人的自大心态;固守旧习,又因属“华”而难以掩饰民族的自卑心态。由此,“西崽”就成了既自大又自卑,既媚外又惧外,既洋派又守旧的矛盾结合体,成了半殖民中国二重性的写照。 半殖民中国主奴社会结构中的“西崽” “西崽”活跃于上海、汉口、香港等殖民性的城市。在租界化的上海,知识精英以及买办、西崽等群体容易滋生崇洋的心理。年吴趼人就曾感叹:“买办也,细崽也,舆人也,厨役也,彼其仰鼻息于外人,一食一息,皆外人之所赐也,彼之崇拜外人,不得不尔也。……胡为乎俨然士夫饱经史、枕典籍者,亦甘侪于此买办、细崽、舆人、厨役之列,而相与顶礼崇拜也?”盲目崇洋的心理,进而推动了“欧化”的风潮。郁慕侠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欧化风尚进行了描述:“现在一般摩登的青年和有钱的富翁,不但对于衣、食、住、行都崇尚欧化,即如起居一切、语言动作,也仿效西式。”崇洋、欧化的风尚与殖民权力在中国内部构成了同谋关系,对人群进行界分,并改变了中国既有的阶层关系。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大都市的半殖民权力结构。 鲁迅曾多次对上海和香港的种族、阶层关系的殖民性质进行评说。第一次是年2月19日在香港青年会的讲演,演讲的主旨是反对“保存旧文化”,认为高唱赞美中国文化的“老调子”的,无论洋人还是国人,都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 上海是:最有权势的是一群外国人,接近他们的是一圈中国的商人和所谓读书的人,圈子外面是许多中国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将来呢,倘使还要唱着老调子,那么,上海的情状会扩大到全国,苦人会多起来。 第二次提到是年9月28日,鲁迅乘船经香港前往上海,一个西洋人带领几个中国属员以搜检行李为由,敲诈勒索,存心捣乱,蛮横无理。他因此感慨: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 第三次提到是年5月22日,鲁迅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演,批判革命文学的无根柢,从而呼吁多介绍外国的文化和文艺,顺便又谈到了主从关系的上海权力圈: 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是有些落后。新的事物,都是从外面侵入的。新的势力来到了,大多数的人们还是莫名其妙。北平还不到这样,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 在鲁迅所描画的上海和香港种族权势的圈层图中,中心为洋主子,接近洋主子的是高等华人和西崽,圈子外面是普通中国百姓。在这样的圈层图中,就会出现鲁迅所批判的“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中外合谋的主奴社会结构心怀不满,由此推导出的观点却指向批判中国文化、提倡西化。鲁迅的观念反映了自晚清以来半殖民中国所陷入的文化怪圈。 殖民地知识精英的处境内含难堪的悖论:“由仰慕而至仿效,等于就是赞同殖民化,这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受殖者一旦顺应了自己的命运,也就坚决否定了自己,换言之,他是以另一种方式否定了殖民者的现实。否定自我和爱慕他人,是一切欲求同化者的共性。以此寻求解放的人,这两方面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对殖民者的爱慕中,潜藏着以己为耻、自我怨恨等等复杂的心态。”不过,中国知识分子最初“主张西化的初衷,其实恰恰来自民族主义的情绪,据说是不想让中国人‘万世为奴’”,他们的民族主义属于“反传统的民族主义”。在鲁迅,无论是早期提倡的“任个人而排众数”,还是后期的阶级观念,都把民族国家当作“个人”和“民众”的对立面。从“立人”来看,鲁迅主张西化,持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立场,理由正当,但是,把遗弃民族文化、模仿西方当作出路,并不能解决半殖民中国面临的悖论。 西化与殖民化、反殖民与民族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西方文化优越观在中国的确立即意味着此时‘西方’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既定组成部分”。半殖民中国面临的世纪性难题是,既要模仿西方(模仿即意味着对西方权威的承认),又要去除嵌入中国内部的殖民权势,这就造成中国文化的发展在西化与民族化之间摇摆不定的情状。 近代知识分子提倡“向西转”,具体分化为两种观念路向:“一个是普遍的世界主义观念”,这种观念“相信世界必然向一个类似于西方列强的方向发展,中国也不例外”;“一个是个别的民族主义观念”,这种观念“相信只有民族和国家的强大,才能够与列国一同存在于世界的现代秩序内,中国当然也不例外”。这两种观念尽管存在不一致,但也可以沟通,这就是葛兆光所指出的:“在普遍向西转追随世界主义的大势背后,又隐藏着相当深的民族主义取向。”鲁迅担心的不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而是担心多数人执意保存“国粹”,中国人将“要从‘世界人’中挤出”,难以存续,因此他提倡西化,以“普遍的世界主义观念”来抵抗“个别的民族主义观念”,既否定中国文化,又批判中国人的奴隶根性。 把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关系整体性地理解为“奴”与“主”的性质,在清末比较流行,五四落潮后已淡化。鲁迅却从五四到三十年代,一直持“逆向种族主义”的态度看待中西种族关系和半殖民中国的文化人格。而且鲁迅认为“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对西方文明的企慕与对中国文化的否定,以及对上海租界乃至民族国家的主奴结构的理解,使得鲁迅把批判的笔锋指向了“西崽”现象。需要说明的是,鲁迅对“西崽”的批判,同时使用了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观念武器。 对“西崽”的批判,隐含着半殖民地知识分子的文化义愤,《民族与民族主义》中的一句话可以挪移过来解释这种半殖民义愤:“对文化差异的惊讶很容易变成对混合的厌恶,或者变成对差异等级的赞扬。”鲁迅信奉中西文化的优劣差序,厌恶“染缸式”的混合,故对社会身份、文化心态处于华洋、主奴之间的“西崽”极为不满。 中外冲突、西化、民族主义与“西崽” 在回应林语堂对左翼“西崽”的批判之前,鲁迅就把上海的巡捕、门丁、西崽和“高等华人”都当作“西崽”。《“揩油”》一文写到:“西崽”“大抵是憎恶洋鬼子的,他们多是爱国主义者。然而他们也像洋鬼子一样,看不起中国人,棍棒和拳头和轻蔑的眼光,专注在中国人的身上”。《“以夷制夷”》讨论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方法时,鲁迅提到“对付下等华人的有黄帝子孙的巡捕和西崽,对付智识阶级的有‘高等华人’的学者和博士”,把巡捕、西崽和“高等华人”当作一丘之貉。如果联系“五卅惨案”中鲁迅撇开民族主义来谈“文明”问题的态度,我们就能理解鲁迅的特异思想。 鲁迅早期主张中西文化的融合,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年12月谈到陶元庆君的绘画时也说:“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但更多时候,鲁迅并非持“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观点。一方面,鲁迅一直不遗余力地攻击“国粹”“国故”“读经”,观点激进而尖锐,如“废汉文”,“不读古书”,“吃人”文化,两种“奴隶”时代,等等。另一方面,鲁迅是“向西转”的积极倡导者,认为要救助“衰老的国度”,“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他早期从“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出发,认为把西方文明中的“物质”“众数”观念“横取而施之于中国则非也”,但后来主要担心国人不能模仿到西方文明的真义。他对西方文化的中国化情形颇为不满,感叹“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无不失了颜色”。中国人“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化为济私助焰之具”,“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他认为西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外来的东西,单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车也须有好道路,一切事总免不掉环境的影响”。 当西化与民族主义相冲突时,鲁迅选择的是西化。“五卅惨案”发生后,鲁迅在《忽然想到》(十节至十一节)中把这一帝国主义的暴力事件转换为“文明”的思考。“五卅惨案”在上海乃至全国激起了强烈的反殖、排外、抵制洋货的运动,是民族主义意识全面觉醒的标志性事件。但鲁迅担心反殖、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会把“西方文明”一起排掉鲁迅年发表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也表达了这种担忧:“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因此,他所采取的基本立场不是反帝、排外的民族主义,而是借此表达对西化前景的担忧。在文中,他以反向推导的方式,得出英国给中国带来了一些“真文明”:“上海的英国捕头残杀市民之后,我们就大惊愤,大嚷道:伪文明人的真面目显露了!那么,足见以前还以为他们有些真文明。”并认为“英国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为了进一步确立这一观点,鲁迅以中国内部的屠杀来佐证:“中国有枪阶级的焚掠平民,屠杀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抗议。莫非因为动手的是‘国货’,所以连残杀也得欢迎;还是我们原是真野蛮,所以自己杀几个自家人就不足为奇呢?”既然“自家相杀”,也就难免为异族所打。如此类比和推论,近似于帝国主义关于西方文明/殖民与中国传统/野蛮的观念。清末的梁启超还分不清殖民与西方文明的界限,故偏激地认为:“苟能自强自优,则虽翦灭劣者弱者而不能谓为无道。何也?天演之公例则然也。我虽不翦灭之,而彼劣者弱者终亦不能自存也。以故力征侵略之事,前者视为蛮暴之举动,今则以为文明之常规。”这种进化论与殖民政策合谋的论调,在清末时期就已被批判:“呜呼!斯欧美人所以挟至惨极酷之殖民政策,役其人,占其产,窘其生命。巨憝滔天,讼而得直。哲学家为之揭爰书曰:适者固宜尔也。” 如果不涉及殖民暴力事件,史书美的观点可以为鲁迅的西化观念辩护:启蒙知识分子把“西方”区分为“都市西方(西方的西方文化)和殖民西方(在中国的西方殖民者的文化),在这种两分法中,前者被优先考虑为需要仿效的对象,同时也就削弱了作为批判对象的后者。通过这种两分,知识分子可以倾向西化却不会被看成是一个卖国贼,他变成了民族主义者/卖国贼两分之外的第三种人”。然而,史书美同时指出,“通过文化启蒙话语来遮蔽殖民现实的做法正是半殖民文化政治的地区性特征”。在半殖民中国,其实很难脱离民族主义来谈论“文明”问题,在文明/殖民与民族国家尖锐对抗的事件中,文化上的西化观念往往需要暂时避让政治民族主义,或者与政治民族主义结盟,既提倡“都市西方”,又批判“殖民西方”,而不是在谅解“殖民西方”的前提下提倡“都市西方”。 鲁迅一再坚持认为“要别人承认是人,总须在自己本国里先争得人格。否则此后是洋人和军阀联合的吸吮,各处将都和香港一样,或更甚的”。不过,殖民暴力加剧了民族内部的压迫,同时,殖民暴力也不会因为内部压迫的消失而自动终止,这实际上涉及公民的国家与民族的国家的关系问题。从殖民、半殖民国家的历史看,只有先成为独立自主的“民族的国家”,才能进一步发展为“公民的国家”和“人之国”。而“民族的国家”只有通过反殖民才能实现。 本文讨论鲁迅与“西崽”的问题,却旁逸斜出,转而说到中外冲突中鲁迅的态度,看似跑题,实则不然。鲁迅对“西崽相”的鞭挞,所持的就是民族主义的钢鞭。“政治上的反帝斗争,往往被认为是反殖斗争的同义语”,“反殖运动在文化层面上的诉求,往往就是民族主义”。但鲁迅不是把民族主义用于反殖民事件,而是用于民族国家的自我批判和对欧化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张福贵认为,“民族主义的社会功能是与一定的历史境遇分不开的,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民族主义思想可以凝聚人心同仇敌忾,势必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愈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下,世界主义思想才愈是不可或缺的。这不仅体现出一个民族的胸怀和视野,而且也决定着一个民族性格的构成和文化发展的方向。吸收和坚守这一思想,是促使传统文化尽快转型和世界影响力扩大的最佳途径。”如果脱离鲁迅在国家冲突事件中的具体反应,脱离中国的半殖民语境来看,那么,从这一观点对鲁迅所做出的辩护,是极有眼光和说服力的。然而,鲁迅对事件的解说,与“致人性于全”并无关系,使用的是民族政治话语而不是有关“立人”的思想话语。由于鲁迅面对中国的半殖民境遇,他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矛头基本上是内指的,指向国内的执政府、统治阶级以及帝国的帮凶,因此,“西崽”就成了鲁迅加以批判的恶名。 半殖民中国领土主权的基本完整,使得“反传统的民族主义”和“西化”的文明观都有“民族国家”作为凭借。鲁迅把本民族国家看作一系列负面品质的汇聚,由此而把帝国主义的残暴事件转化为要求文明进步的话语表述。我们既可以从半殖民中国的文化语境出发,把它解释成包含深层次矛盾的“东方型民族主义”,也可以从“维护经典与传统的‘原教旨的民族主义’”出发,把它看作“西崽”人格的表现。 鲁迅、林语堂关于“西崽”的论争 鲁迅、林语堂在北京和厦门时期是文坛盟友,到上海后两人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最终闹翻,这主要是性格差异和观念分歧所致。正如王兆胜所指出,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林语堂,最终不能忍受鲁迅的“多疑”和“霸气”,鲁迅站在“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角度批判林语堂的小品文和幽默观,也与林语堂从“文学性功能”看待文学大相径庭。两人冲突的高潮便是关于“西崽”的论争。林语堂写了《今文八弊》,鲁迅随后以《“题未定”草》来回击。 林语堂的《今文八弊》分上、中、下三个部分先后刊登在《人间世》半月刊,上、中两部分发表后,鲁迅即写了《“题未定”草(一至三)》予以回应,故本文讨论鲁、林关于“西崽”问题的交锋,只介绍《今文八弊》的上、中两部分。《今文八弊》为林语堂有感年代中国文坛的种种弊端而写,林语堂写作此文不仅秉持“以箴其失”的态度,而且还提出了“救之之道”。《今文八弊(上)》为提出问题的部分,在这一部分,林语堂阐述了中国文化“东壁打到西壁”的纷乱浮躁:“国中的思想忽而复古,忽而维新”,“各有成见派别”,“乱嚷乱滚不得安静”,文化观念迷乱,“只有冲突,没有调和”,难以“融会古今,贯通中外”。“东壁打到西壁”的文化观念影响到文学,带来了“今文八弊”,《今文八弊(中)》语堂:《今文八弊(中)》,《人间世》阐明了前四种:(一)方巾作祟,猪肉熏人;(二)随得随失,狗逐尾巴;(三)卖洋铁罐,西崽口吻;(四)文化膏药,袍笏文章。“今文八弊”的指陈,既是林语堂对左翼阵营一年来的批判的总回击,也是对自己提倡幽默、小品文的辩护。结合鲁迅在上海的生活体验和创作经历,可以发现林语堂所指陈的年代文坛的四个弊端,好些方面或明或暗对鲁迅构成了嘲讽,如:怕落伍,赶时髦,否定中国文化,“耻为华人”,对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前后不一,“门户之见”,“动辄以救国责人”。有些方面,鲁迅可能难以辩驳。因此,鲁迅对林语堂的反驳,只是避重就轻,并没有真正回应林语堂措辞尖锐的指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林语堂与鲁迅对“西崽”的看法,同大于异,因此鲁迅也没必要一一加以辩驳。 鲁、林关于“西崽”问题的交锋,充满了火药味。与林语堂从文化上、文学上揭批左翼文人的“西崽”心态不同,鲁迅在《“题未定”草》中所作的是道德人格、民族政治上的指控。尽管林语堂在《今文八弊》中声言“大家都是黄帝子孙,谁无种族观念?”但仍被鲁迅扣上了近似“卖国文人”的“西崽相”的帽子。林语堂对“西崽”文人的批评,主要指向竞角摩登、仿效西洋和鄙弃传统、耻为华人的洋奴心态。鲁迅的反驳建立在所引《今文八弊(中)》两处文字的基础上。第一处为“(三)卖洋铁罐,西崽口吻”这部分的最后三句话,其实从中也没有引申出有力的辩驳,只是以之作为引子,引出作为职业的“西崽”——会说英文,以服侍洋东家为职业,同时又是“国粹家”,装扮华洋结合。再由此转向关于“西崽相”的阐发: 西崽之可厌不在他的职业,而在他的“西崽相”。这里之所谓“相”,非说相貌,乃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包括着“形式”和“内容”而言。这“相”,是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租界上的中国巡捕,也常常有这一种“相”。 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这就是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鲁迅在这里对“西崽”的阐释,与林语堂以及其他作家的看法有类同之处,那就是“西崽”兼有崇洋媚外和重视国粹的特性,其出彩之处在于“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这一经典表述。不同之处是鲁迅所塑造的“西崽相”不仅在华人面前自大,也在洋人面前自大,其他作家笔下的“西崽”则既自大(对华人)又自卑(对洋人)。但紧接着,鲁迅从历史中扒出“事大”这一特性,添入“西崽相”的内涵中。“自大”与“事大”的结合,是鲁迅对“西崽相”内涵的独特解读。不过,《“题未定”草》行文至此,对林语堂指责左翼文人为“西崽”的反驳,显得力量不够。往高处说,可以解释为鲁迅赋予了“西崽相”以普遍性的文化内涵;单就论争而言,鲁迅还是在外面绕圈子,未能真正回应林语堂对左翼“西崽”的批判。 鲁迅引用的《今文八弊》的第二处文字为“(二)随得随失,狗逐尾巴”这一部分的最后三句: (今人所要在不落伍,在站在时代前锋,而所谓站在时代前锋之解释,就是赶时行热闹,一九三四年以一九三三为落伍,一九三五又以一九三四为落伍,而欧洲思想之潮流荡漾波澜回伏,渺焉不察其故,自己卷入漩涡,便自号为前进。其在政治,如法西斯蒂在欧洲文明进化史上为前进为退后,都未加以思考。)其在文学,今日介绍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二究竟。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叹女儿身,事人以颜色,其苦不堪言。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 鲁迅的引用属于断章取义,括号(笔者所加)里的文字鲁迅并未引述。林语堂的这些文字主要指向怕落伍而盲目追赶外国潮流的文坛风气,而鲁迅把表意的“帽子”摘了,专在“波兰诗人”“捷克文豪”与“英法美德文人”的关系上做文章,抓住了林语堂论述的漏洞。由此,鲁迅既避开了直接回应“不落伍”问题,又可以现身说法,声明“绍介波兰诗人”是多年前的事了,暗示与赶时髦无关,也就与“媚”无关。紧接着,鲁迅以“借题发挥”的论辩技巧,把译介外国文学的问题转换为民族国家的政治问题: 诚然,“英美法德”,在中国有宣教师,在中国现有或曾有租界,几处有驻军,几处有军舰,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使一般人仅知有“大英”,“花旗”,“法兰西”和“茄门”,而不知世界上还有波兰和捷克。但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打过北京,那文学却在,不过有一些人,并未“已经闻名”而已。外国的文人,要在中国闻名,靠作品似乎是不够的,他反要得到轻薄。 所以一样的没有打过中国的国度的文学,如希腊的史诗,印度的寓言,亚剌伯的《天方夜谈》,西班牙的《堂·吉诃德》,纵使在别国“已经闻名”,不下于“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国却被忘记了,他们或则国度已灭,或则无能,再也用不着“媚”字。 由此,鲁迅把林语堂抛出的“西崽”的“媚”和“奴”的恶名加以升级,奉还给了林语堂。平心而论,林语堂对左翼“西崽”的论述,尽管措辞激烈,仍属对文坛具体状况的针砭和对自我文学观念的辩护,而鲁迅的反驳则超越了文化、文学论争的界限,借用了超强的民族政治话语,最终营构出林语堂“认敌为亲”或“为王前驱”的“西崽相”。 结论 对鲁迅、林语堂等作家做出是否属于“西崽”的论断,并没多大意义。因为半殖民中国的文化语境,几乎在所有作家身上或浓或淡抹上了“西崽”的痕迹。这就出现了“西崽”批判“西崽”的现象。表面看来操持此话语的知识分子将陷入“五十步笑一百步”的尴尬境地,但实际上,知识分子通过批判策略的选择,回避了批判者的身份错位所带来的尴尬。一是启蒙话语赋予了知识精英言说的正义性。在半殖民中国,“西崽”穿梭在华洋之间,是中西文化在表层进行混杂的产物,知识分子便以思想启蒙的名义,立足于一端——中华的立场或彻底西化的立场,对“西崽”新旧合污的文化人格进行批判。二是知识精英占据了国族立场和道德批判的制高点。在民族大义和道德武器的审判之下,知识精英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俯瞰“西崽”,而他们自身似乎成了不被殖民现实玷污的民族主义者或正宗西化者。对“西崽”的批判,也是知识分子自身的殖民性焦虑的释放,包括对“以夷变夏”的惶恐,对“酱缸文化”的担忧,对殖民权势的拒斥和对中外主奴关系的忧愤。总之,“西崽”是半殖民中国文化人格的典型形态,对之构形所采用的话语,同样植根于半殖民中国的文化语境,释放的是半殖民中国的文化焦虑,最终通达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愿景。 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在清末民初时期有着中国与西洋的界分,“西洋文明”作为一种令人既爱又恨的文明被知识分子加以倡导,并被置于中西二元框架中来认知,作为中西文化混杂产物的“西崽”成为华夏中心主义、种族革命观念和仇洋心理的泄愤对象。五四时期,带有殖民色彩的“西洋文明”在启蒙视野下转换为“现代文明”,西与中的文化关系在认知中转换为新与旧的关系,知识精英一心提倡西化,自然不会对与“洋”沾边的“西崽”说三道四。五四之后,知识精英开始从“现代”的角度反思殖民色彩的“西洋文明”,民族意识的张扬和民族传统的复兴也加剧了对殖民西方的不满,“西崽”在这种文化语境和心态中被再一次推向审判席。因此,“西崽”除了在五四文学中处于缺席状态,其他时期构设的“西崽”都属于中西合污的人物,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文化激进主义者、西化立场者和民族主义者、阶级论者和反殖民者共同指责的对象。 “西崽”不仅被当作半殖民中国的一种文化人格,也被当作道德武器加以运用。林语堂和鲁迅相互攻击对方为“西崽”,都带有作为道德武器和攻击手段加以运用的成分。年鲁迅写到: 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或者要说,我们现在所要使人愤恨的是外敌,和国人不相干,无从受害。可是这转移是极容易的,虽曰国人,要借以泄愤的时候,只要给与一种特异的名称,即可放心剚刃。先前则有异端,妖人,奸党,逆徒等类名目,现在就可用国贼,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 把半殖民中国的民族主义怨愤转移到同胞身上,屡见不鲜。现代作家对“西崽”的批判,很大程度上也带有这种色彩,“西崽”成了中国半殖民境遇的替罪羊,无论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是激进的西化知识分子,都对古老的、民族的中国遭遇现代的、殖民的西方后,所产生的中间物“西崽”心怀不满。攻击鲁迅的文人,常用此招。鲁迅也深谙此道。他批判林语堂等高等华人的“西崽相”时,夹枪带棒,关于外国文学译介问题的解说夹杂着“八国联军”侵华、黄浦江中的外国军舰之类的殖民史实,暗示西崽文人是殖民帝国的帮凶和奴才,是“里通外国”的汉奸;批判“民族主义文学”时,把“民族主义文学家”说成是“帝国主义”的“奴才”“鹰犬”,所作所为于帝国主义有益,他们是“为王前驱”,“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相关”。对于半殖民中国而言,“中国人最强烈的感情是痛恨外国人”,而“中国最有力的行动是崇拜外国人”。这就注定中国文化的发展在民族化与西化之间摇摆,难以简单解决其“深层次的矛盾”:“‘它对被模仿的对象既模仿又敌对’。它模仿,因为它接受外国文化所设定的价值观。但它也拒绝,‘事实上有两种拒绝,而两者又是自相矛盾的,拒绝外国入侵和统治者,却以他们的标准模仿和超越他们;也拒绝祖先的方式,它们既被视作进步的阻碍,又被作为民族认同的标记’。”“西崽”也是这一“深层次的矛盾”的产物之一。 现代文坛虽然分为新与旧、中与西、日俄派与欧美派等文化阵营,但是,无论知识分子持激进还是保守姿态,都试图在现代化与殖民化、西化与民族化之间寻求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在评析、理解现代作家中西、新旧文化论争时,在讨论“西崽”现象和评论“谁是西崽”的问题时,尤其涉及到“民族主义”超强话语的使用时,要避免“落入自我想象和观念预设的陷阱”,只有回到现代中国的半殖民文化语境,才能做出理性的解读。 刊名:《求索》 主管主办: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编辑出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期刊社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ousongjiea.com/ysjtx/416.html
- 上一篇文章: 总有人问我当老师是什么感觉今天统一回复
- 下一篇文章: 油松花粉的保健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