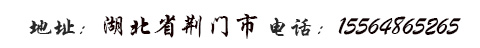前世安排的赴约bull初相遇
|
在哪儿治疗白癜风好 https://m-mip.39.net/nk/mipso_4334853.html 很多年以前,这里是一片草原。就和现在差不多,这里住着一个英俊的牧马人,他养的马比天上的马还要神骏,他天天在这里牧马,吸引了天帝的女儿。她被他的勇敢和善良所吸引,化身牧女和他相会,可是好景不长…… 我们能否到达彼岸,以拯救我们的灵魂。 我喜欢行走,行走能让我的心静下来,获得无上的欢喜。 其实,路的尽头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走这一程。 我从未想到,我的东北之行是在赴一个前世就注定的约会。 我走的那天天空飘着雨,七月。 雨轩说:“我们的灵魂封印在一片静默的湖中,我们需要冲破孤寂的水到达彼岸。” 我说:“彼岸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雨轩说:“彼岸的世界就是放下一切,觉行圆满。” 我们从未见面,皆因为我们的缘分未到。 我们隔着几万里的时空还能感受到对方,皆因为我们前世在三生石前的誓言。 我们无法舍弃灵魂两端的牵挂,不是我们放不下,是因为爱的诱惑超过灵魂的永生。 从北京登上列车,过了山海关,已经能够感受到来自辽东大地上的风了,那是一种马群掠过大地的感觉,风驰电掣,奔雷闪电,仿佛灵魂一瞬间深入了这片土地,触摸到了大地深处的颤抖。 我隔着窗,望着天空的云,它们高傲的看着我。天空低垂,厚实的巨型云块悬浮着,仿佛一座又一座城堡。天空下的大地一望无垠,一条河流将大地一分为二,河水呈浅靛蓝色,像用画笔勾勒出来似地。 河岸的这一边,一个牧人赶着一群羊去饮水,羊儿们聚集在一起,仿佛在商议什么。河岸的那一边,金黄的麦茬间飘荡着翠绿的草杆儿。几棵孤独的树木在原野上亭亭如盖,静默不语,宛若处子。 更远的地方,也许是村庄,隐隐约约是一片屋顶和撑起电线的水泥杆子。村庄的背后,是起伏的群山,云影落在山脉上,壮观极了。 我靠着火车的车窗,看着窗外风景不断变幻,打起了盹儿。不知什么时候,竟然睡着了。 深夜,手机铃声猛然响起。接通电话,雨轩问我:“睡了吗?” 我一直在纷乱的梦里,恍然间听到她的声音,犹疑在梦中,好一阵子没有反应过来。我抬起腕上的迪沃斯防水手表,是凌晨1点。 我低声说:“难道你这会儿还没睡?” 她用甜美的声音说:“睡了一觉醒了,想你了。我们聊一会儿好吗?” 我说:“好。” 我们的灵魂遥相对应,寻找着清澈的眼睛,期望发现出口,或者入口。 火车窗外下起了大雨,噼哩啪啦的砸在玻璃上,黑漆漆的夜色中不知是山的影子,还是树影。匍匐着,似乎要撞破玻璃,撞进我朦胧的梦里来。 一夜醒来,已经能够感受到冰和雪的清冽,我已经把白山黑水踏在脚下,我的眼里是早晨清透的阳光。 抹掉浪漫化的光环,直面现实生活的平庸,我们是否能够毫无保留的相对? 我不断勾画她的影子,回忆她的声音,在早晨,在傍晚,在深深的暗夜,她的声音好像清亮的泉水,欢快的流进了我的心里。她的声音是如此的轻柔,如此的欢悦,如此得一尘不染,聆听她的声音仿佛隔水闻琴,心刹那间平静下来,平静中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欢喜。 现在,我马上就要和她见面了,不是梦里,而是一个真实的人儿,立体的人儿。 我们经常写信,有时候写完一封立刻又开始写下一封。她说,快来救救我吧,我太想你了…… 雨轩,我来了,不仅来救你,也期望你能拯救我。 火车停下了,我的脚真切的踏在了这片土地上,停在了中国东端太阳升起最早的一个城市——鸡西。这是一个宁静的小城,经过一场大雨的洗礼,远处的山棱角分明,有几分透剔的感觉。 透过火车站的巨大的玻璃门,我已经看见了她,雨轩。 她静静的站在车站外,仿佛清晨的一株白杨,挺拔的身姿无比曼妙。她嘴角微微上弯,带着笑意看着我,因为走出车站的只有我一个人,而接站的也只有一个她——仿佛这个世界只有我们两个。我们注视着对方,仿佛在印证一种记忆。 雨轩的眉毛细长秀气,眼睛清澈的仿佛流溢的山泉,眉宇间透着灵性。她上身穿着白色的T恤,下身穿着淡雅的牛仔裤,牛仔裤上暗绣着孔雀图案,脚上是缀着一串珠子的小皮鞋。头发散散的披着,既没有戴耳环,也没有戴项链,除了手腕上古典的藏银手镯,几乎看不到任何饰物,不施粉黛,一副素面朝天的样子。 我们的目光交汇,她的脸慢慢的飞上一片红霞,眼睛羞怯的躲闪开来,低下了粉颈。 雨轩说:“走吧。坐了两天火车,应该很累了。”她的声音清脆悦耳,比电话里的声音更加真切。 “嗯。”我点点头。 雨轩招手,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我坐进车里,她安静的坐在我的旁边。身上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幽香,若有若无。车子上了大道,她始终不敢转过脸正视我,眼睛里却漾着笑意,嘴角挂着两个调皮的酒窝。 她指着窗外的风景一路为我介绍着,车子没有进市区,而是在拐了个几个弯之后进了一片树林,树林里零星住着人家,我仿佛闯进了童话的世界——这是一条通往森林里公主殿堂的路上。 车子在林间不断的转弯,最后上了一条陡坡路,路的两边堆放着大量砍伐下来的树木,一股新鲜的木料的味道在鼻翼萦绕。进入林子的深处,那里隐着一片街区,我真怀疑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就好像远古的那些动人传说一样,我被一个仙女带进了她的世界。 我正沉迷于幻想中的时候,雨轩说,到了。 我们下了车,她带着我上了一栋布满爬墙虎的二层小楼,小楼内的布置略微有点日式风格,木质的方格窗子,地上铺着榻榻米。实木门上装饰着简单的木格子,挂着几幅富士山内容的浮世绘,可能是葛饰北斋《富岳三十六景》的印刷品。上了二楼以后,穿过一条短短的楼道,尽头就是雨轩的房间。 她的房间雅致干净,有淡淡的香味,靠北的墙边是一张硬木雕花小床,床上铺着淡蓝色的床单。东边的墙上是窗子,窗子上是蓝色的带格子的窗帘,窗下是一张写字台,上面整齐的放着外文书籍,笔筒。 她伸手拉开窗帘,阳光肆无忌惮的闯了进来,整个屋子变得通透明朗,她精致的脸庞仿佛也是透明的,闪烁着水晶一般的莹润。从窗口向外望去,窗外是绿色的原野,浅绿、翠绿、深绿,墨绿,到了更远处似乎变成了黑色,像铺开在大地上的绿色色谱,呈现出惊艳的色调。 她指着窗外几乎是天际的地方,轻声说,那里,在那里,你看见了吗?有一个小湖。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绿色的原野上果然闪烁着一片莹光,仿佛一块蓝色的宝石。 我回头望着她,尝试着握住她柔弱无骨的手,她含羞望着我说:“我先去给学生上课了,两个小时就回来,你先睡一觉,等着我啊。”说完,抽出手,拉上门跑了。我笑笑,就势躺在床上,嗅着淡淡的香味,我慢慢的闭上眼睛。刚刚进入朦胧状态,好像有人在给我盖被子,我猛地惊醒,雨轩笑意盈盈的望着我。 “你怎么回来了?”我说。 雨轩举起腕表到我的眼前说:“你看,我都上了一个上午的课了。我还以为你会醒。一下课我就赶紧跑回来了,学校放假了。” “我感觉刚睡着。我们接下来干什么?”我说。 “你说呢?”她诡秘的望着我。 “由你来决定。”我说。 她走到书桌前,拿起一本旅游地图册。翻到夹了书签的地方给我看,她在鸡西、密山、虎林、兴凯湖、东宁、绥芬河等六个地方画了圈,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日程安排。 她指着窗外远处的湖说:“我们今天去那湖滨吧,你看钓鱼怎么样?” “那真是再好没有了。”我说。 “我去准备钓具,你最好现在填饱肚子。”她把筷子递给我,又打开了饭盒,饭盒内分成三个格,一个格子里是煎鸡蛋,一个格子里是煮面条,另外一个格子里是一份汤。我望着硕大的饭盒说:“这么多。” “好像是多了点,不过不吃饱肚子,那有力气出去玩,多吃点也是好的。”她调皮的笑着说。 我乖乖从命。 吃完饭,我俩带着装钓具的帆布袋、收纳鱼儿的小塑料水桶等物件儿,穿过麦田,踩着泥泞的小路朝那湖边走去,荒野里的路很窄,路的两边长满了齐及人肩的荒草,就是这所谓的“路”上也被一些灌木覆盖着,偶尔还会有一道沟壑,上面搭着简易的木板桥。 我俩小心的走在泥泞的路上,她紧紧的跟着我,和我隔着一小步距离,我能听到她的呼吸,能闻到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幽幽香气,我只要一伸手就能够着她。前面是一道八九米宽的深沟,上面搭着裂了缝的木版,似乎随时有塌掉的可能,我试探性的走上去,木板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雨轩迟疑的望着摇摇欲坠的木板,眼里有些担心。 我向她伸出手,她会意的一笑,轻轻地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微微有些凉,细腻温润,令人怜爱。走到桥的中间,木板大幅度的晃荡起来,她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不要紧,结实着呢。” “嗯”,她还是抓紧了我的胳膊。 我们在灌木丛里穿行,高及人肩的蒲草划过裸露的胳膊。一阵强劲的大风吹过,草木瞬间弯下了腰,大片的云从树冠顶上澄澈万里的天空突突的冒了出来,一块一块的云团在天空铺散开了。棉花团子似地云彩真的太白了,衬托的天空蓝的简直刺眼。我俩只顾仰头看着天空,没有注意脚下,忽然听得一阵扑棱棱的声音,一只大鸟飞了起来。我们这才发现差点踩到一种不知什么鸟的鸟窝,大鸟早已飞走,小雏鸟们也在灌木中一阵子乱窜,几乎还没有看清楚,小雏鸟便一个也看不见了。这大约和它们身上的保护色有关。 我们爬上一段陡坡,坡顶上长着几棵巨大的油松,油松边上的几株碗口粗的小松树不知因何缘故被砍断了,满地都是木头渣子,散发着十分浓烈的木材的味道。我们在巨大的油松树下站了一会儿,就看到一只小松鼠探头探脑的在不远的一根树枝上窥伺着我们。小松鼠的腮帮子鼓鼓的,显然塞满了食物。看着它滑稽的样子,我赶紧举起了相机,它恐怕误解了我的行为,未等我按下快门就逃的不见踪影了。 “是只金花鼠呵。”雨轩说。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金花松鼠?”我问道。 “对呀,你看它背上的花纹,多漂亮。”雨轩感叹的说。 “可惜、可惜。居然没拍到。”我说。 “等等也许还会出现。”她说。 我俩站在松树下,用目光搜寻着每一根树枝,仿佛是开启了生物雷达进行扫描。不一会儿,我又看到一只松鼠,不过我不确定是不是金花鼠。雨轩显然也看到了,她看到我兴奋的样子,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轻声“嘘”了一声,示意我拍下来。我拍了给她看,她努着嘴说:“可惜不是金花鼠,不过这也比没有拍到强。” 我们又往前走了一段路,雨轩用下巴朝远处的一株树上努努嘴,我一看,那里有一个似乎是金黄的影子,赶紧举起相机,同时调焦。拍是拍到了,可是太着急了,镜头是虚的。 “拍是拍到啦,可惜拍坏啦。”我说。 “金花鼠就是这样,尤其是野生的,机灵的很那。没拍到也不打紧,反正你看到它的样子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陡坡的右侧有一条溪流,在草丛里潺潺的流着,把手伸到水里,冰凉冰凉的。 “这条溪说不定是流向湖里的呢。”我说。 “差不多。我们就沿着溪流走好了。” 我们顺着溪流走了一段,前面出现一大片沼泽地,沼泽里咕嘟嘟的往外冒着水。一股独特的,只有沼泽地才有的味道传来,然而并非臭味,而是一种混合着腐烂植物和风的味道。大片的云影落在沼泽里,流溢着一种荒凉的美。 沼泽地挡住了去路,我们只得原路返回,寻找原来的路径。就这样,我们步行了大约三公里,终于在灌木丛里找到了一条路,又胡乱走了一阵子,才终于到了一大片开阔的荒地上,地上长满了矮牵牛、鸢尾、马兰草、蒲公英、天星之类的植物,一派草木丰茂的模样,真是令人高兴极了。这片开阔地原来很可能是一片林子,有不少树桩,还有遗弃在草地上的的树干,已经半朽了。我们在一截树干上坐了下来,略作喘息。 雨轩说:“我好像是带错路了,你不觉得这地方没意思?” “怎么会,这地方很有意思。我就喜欢在这荒草野地里乱逛。照董桥先生的说法,节外生枝多走一趟是小说,有条不紊一程到家是论文。咱这算是编了一部好小说。”我说。 她笑了起来,淡淡的说:“两年前我和阿敏去过湖边一回,这就把路给忘了,你看我这脑子。” “都隔了两年了,何况是只走过一回的路,搁谁都一样。”我安慰她。 我们到了湖边,我彻底被这一片水吸引了,它是如此的静美,仿佛是上天的一滴眼泪,静静的镶嵌在那里,独自忧伤。我走过北半个中国,见过气质各异的河流湖泊,见过势如奔雷的壶口瀑布,见过一泻千里的长江,见过纤秾的瘦西湖,见过澄澈万里的青海湖,可是我没有见过这般气质的湖,它是蓝色的,以至于旁边的草木都闪现着蓝,蓝的彻底,蓝的令人感到刺骨,仿佛在丝丝的往外冒冷气。 “这湖叫什么名字?” “天泪湖。” “真的叫这个名字?” “那还有假。” “有什么渊源没有。” “有个故事。” “讲讲呗。” “这是一个关于爱的传说。” 爱是亘古不断的传说。 “很多年前,不知道多少年前……”雨轩调皮的朝我笑笑,一副老奶奶讲故事的可爱模样。我也禁不住笑了。 “很多年以前,这里是一片草原。就和现在差不多,这里住着一个英俊的牧马人,他养的马比天上的马还要神骏,他天天在这里牧马,吸引了天帝的女儿。她被他的勇敢和善良所吸引,化身牧女和他相会,可是好景不长这件事就被天帝知道了,派人抓回了这位羡慕人间情爱的天界公主。牧马人不甘心,率马群去追。天帝大怒,将自己的女儿变成了一座高不可测的冰山,到山前的牧马人伤心欲绝,变成了一条河,终年围绕着冰山,不知过了多少年冰山消融了,像一滴眼泪一样投入了河中,交汇的水刹那间形成一片透明的湖水,牧马人带来的马群也在这里不肯离去,长久地在这里繁衍,在冰山和河流融合在一起的那一刻,万马嘶鸣,全部化作了石头,你看远处的万马山,是不是很像昂首向天的骏马。”雨轩说。 “这故事不会是你编的吧。”我说。 她轻声笑了起来。 我们走到水边,我捡了几块小石子,向水面上扔去,石子在水面上漂飞着,溅起团团水花,无声的沉入了水底。 “你还有这一手,我也来试试。”雨轩学着我的样子,向水里扔石头,却噗通一声直接沉了底儿。 “得这样,平一点往水面上抛,不能直接扔水里。”我递给她一块片状的石头。这次,她打出了一个完美的水漂。一时间高兴的像个孩子,连续向水中打了七八个才罢休。 湖边长满了水草,水鸭子在草棵子中栖息。打出去的石头在水面上“扑扑”的响,惊飞起七八只水鸭子,在水面上盘旋了一阵,重新又落在了清澈透亮的水里,嘎嘎嘎的叫着,在水面上划起一道道波纹。这是我们今天第二次与鸟儿接触,虽然惊扰了它们,但“有惊无险”,是完全无害的,因而它们重新在自己的地盘上游弋了起来。 我们找到一处适合钓鱼的地方,这是一大片水草少,光线好的亮水区。雨轩从帆布袋的小格袋里拿出一卷钓丝,装在伸缩钓竿上,又娴熟的将蚯蚓挂在鱼钩上。这片水面有一股暖暖的小溪注入,溪水注入湖中,翻滚着小小的浪花,水温似乎没有那么冷。鱼钩刚一放入水中,还来不及架好,末端就变弯了。 “不会吧,这么快就咬钩了,可真是馋嘴的家伙。”雨轩说。 我赶紧去帮忙,一条体型细长,呈柳叶状的鱼儿在水面上挣扎,样子看起来凶猛极了。 “小心点,不要太用力,要用柔劲儿。”雨轩说。 “什么鱼,这么厉害。” “好像是一条翘嘴红鲌,这鱼儿可不容易钓到,不过这片水域离城区远,钓鱼的人少,这个点儿正是钓这种鱼的好时候。”雨轩一边和我说话,一边用柔劲儿配合着鱼儿,以免揪断钓线。鱼儿似乎折腾的没力气了,我们徐徐收线,最后将这条差不多有一尺多长的鱼儿纳入了塑料水桶里。 “真是一条好看的鱼儿呀。”我说。 “确实好看,钓这鱼儿可真够带劲儿的。” 我看着塑料水桶里的鱼儿,它的嘴巴翘的可真够像样子,怪不得叫“翘嘴”,它的背部呈浅色的棕,一体儿的银灰色,但腹部是亮亮的银白色,只有背鳍、尾鳍有一点淡淡的红。这大概就是它被称作“红鲌”的原因吧。 “你钓一下。”雨轩说。 “好。”我照她的方式,挂上了鱼饵,费了相当大的力气才将钩子抛入水中。鱼儿们似乎故意和我作对,十几分钟过去了,鱼钩竟然毫无动静。雨轩告诉我,钓鱼不能操之过急,刚才之所以一下子就钓着了,可能是凑巧了,遇到一条饥不择食的饿鱼。我想想她说的也对,便耐心等了起来。时间不知过了多久,就在我昏昏欲睡的时候,我感觉到鱼线在朝湖水深处拉去,我顿时一激灵,惊叫道:“鱼儿上钩了。” “别慌张。”雨轩跑来,跟我一起握住了鱼竿。我们小心的一点一点的收鱼线,有时候又放一些鱼线,就这样一会儿收,一会儿放,终于看到鱼儿露出水面的身姿。好家伙,真是一条大鱼。这条鱼儿的背颜色深极了,粉红的尾鳍在水中看着十分照眼。 “好家伙,又是一条翘嘴吧。”我说。 “嗯。”雨轩紧张的握着钓竿,看样子她不准备给鱼儿任何脱逃的机会。就这样折腾了相当时间,才终于将这条鱼儿收服。 “可累死我了。”她说。 “你休息一会儿吧,让我试着单独钓一条。”我说。 “嗯。”她提起装鱼儿的塑料桶,坐到了远处的一棵松树下面。 有了前面的经验,我很容易就将鱼钩放进了水中。不过,和前次一样,鱼儿迟迟不来咬鱼钩。 钓鱼需要耐心,事实上做任何事也是如此。有过经历,才会发现道理不止是道理那么简单。我耐心的等着,光线逐渐的变淡,几乎太阳要落山了,才终于有鱼儿咬钩。可能是我过于着急,猛然一甩杆子,竟然将鱼儿甩出水面,“啪”的一声将鱼儿摔到身后的草地上了,那是一条比手掌还要短小的小鱼儿。身后面那一片草地湿乎乎的,有浅浅的水,那条小鱼儿在浅水中翻腾跳跃,尾巴打在水草上啪啪的响,似乎想借那浅水逃走,但却被水里的草卡住了,动弹不得。我脱了鞋子,小心的踏进有浅水的草丛里,将它拿了出来。可能是鱼儿活动的时候到了,接下来我钓鱼都顺手极了,连续钓了三条,可惜都是只有手掌大小的小鱼。 “你不累吗?休息会儿吧。”雨轩向我招呼道。 “嗯。”我轻声应了一声。 我们收拾好钓具,找到一处水草稀疏的地方,水边上有几块巨大的石头。爬上石头,石头顶部十分平坦,雨轩挨着我坐了下来,望着湖面上的飞鸟,静静地欣赏着这世外的风景。一对不知名的鸟儿从眼前飞过,在天空留下优美的身姿。 雨轩说:“有时候我也想做一只不知名的鸟儿,你愿意做另一只么?”她歪着头,望着我的眼睛。 “我愿意和你一起,做一对不知名的鸟儿,在这自由的天空飞翔。” 她轻声笑了起来,说道:“你说的像诗一样。” 事实上,几年后我翻看旅行札记,确曾以这句话为由头创作过一首诗,其中有一节: 你喜欢那高而远的星空闪烁的美 相互依偎是最后的麦草 感觉霜落 让我们共同承担这秋意 在这麦子的肩上 在这金黄的铜盘里 你我相逢在村庄 不惧怕山的高也不惧怕湖的阔 秋天注定 我们是一对飞过的鸟 编辑组|刘明清(主编) 白羽(执行主编) 岑红高伟立 本期排版|iwala 联系邮箱: minstrelstory ompbj.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ousongjiea.com/ysjxw/4899.html
- 上一篇文章: 藏药资源概述
- 下一篇文章: 苗圃里杂草横行,用苗安静连封带杀效果好